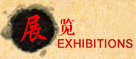北京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紀(jì)念館 秦素銀
1918年9月紅樓建成于沙灘(當(dāng)時(shí)稱漢花園),這座建筑并沒能依照其原建筑目的成為北大預(yù)科學(xué)生寄宿舍,而是成為北大文科、校部和圖書館所在地。1918年也正是近代中國(guó)最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入主北大的第二年,新文化主將們聚集在北大,實(shí)現(xiàn)了北大與《新青年》一校一刊的結(jié)合,從而使紅樓成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運(yùn)動(dòng)爆發(fā),北大師生是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的主要領(lǐng)導(dǎo)與參與人,紅樓見證了五四運(yùn)動(dòng)從爆發(fā)到勝利結(jié)束的全過程,從而成為五四運(yùn)動(dòng)最重要的歷史見證。
一、紅樓的建成與投入使用
1916年,當(dāng)時(shí)的北大校長(zhǎng)胡仁源、預(yù)科學(xué)長(zhǎng)徐崇欽與比國(guó)儀品公司訂立借款合同,借洋二十萬(wàn)元,在原漢花園學(xué)生宿舍東側(cè)修建預(yù)科學(xué)生寄宿舍。[①]1917年9月,一座主體用紅磚砌成的五層大樓拔地而起,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紅樓。1918年2月,學(xué)校將原擬做寄宿舍的新樓“改作文科教室及研究所、圖書館與其他各機(jī)關(guān)之用”[②]。這年9月,紅樓正式落成。這座建筑平面呈工字型,地上四層地下一層,紅瓦坡頂,體量高大,東西面寬一百米,主體部分進(jìn)深十四米,東西兩翼南北均長(zhǎng)34.34米,總面積一萬(wàn)平方米,磚木結(jié)構(gòu),建筑造型為簡(jiǎn)化的西洋近代古典風(fēng)格。底層青磚墻,水平腰線以下,以寬大的水平凹線強(qiáng)調(diào)其厚重感。二至四層為紅磚墻,青磚窗套,角部以“五出五進(jìn)”青磚作隅石處理。檐部以西式托檐石挑出。南立面中央部分墻體微向前凸,項(xiàng)部上折成西式三角形山花,窗戶改為一大二窄的三聯(lián)窗。底部入口為塔司干柱式的門廊。門廊兩側(cè)坡道可供車停至門前。門廳北部為主樓梯。兩翼各有一部樓梯,通往后院。[③]
1918年9月30日,文科教務(wù)處及文科事務(wù)室[④] 搬入紅樓,隨后北大校部各機(jī)構(gòu):校長(zhǎng)、各科學(xué)長(zhǎng)、庶務(wù)主任、校醫(yī)陸續(xù)遷往紅樓辦公。10月2日,北大文科開始在紅樓上課[⑤]。從10月12日起,圖書館開始遷往紅樓[⑥] ,10月22日?qǐng)D書主任發(fā)出公告“本館辦公室一概遷至新大樓第一層,各閱覽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辦公。”[⑦] 圖書館的搬遷工作結(jié)束,意味著紅樓已經(jīng)完全投入使用。
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策源地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職于北大,并開始對(duì)北大進(jìn)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蔡元培認(rèn)為,大學(xué)是研究高深學(xué)問的地方,學(xué)生進(jìn)入大學(xué)的目的應(yīng)是求學(xué),而不是升官發(fā)財(cái)。為改變北大腐敗的狀況,蔡元培從延聘“積學(xué)而熱心的教員”入手,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則,許多不同觀點(diǎn)的教授包括保皇黨(劉師培)、守舊派(黃侃)和自由主義者(胡適)、激進(jìn)派(陳獨(dú)秀)都同時(shí)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學(xué),努力營(yíng)造思想自由的學(xué)術(shù)氛圍,充實(shí)和提高北大的學(xué)術(shù)研究和教育水平。蔡元培能兼容新舊,但骨子里是“趨新”的,就任北大校長(zhǎng)之初就聘請(qǐng)了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主將、《新青年》主編陳獨(dú)秀為文科學(xué)長(zhǎng),又延聘胡適、周作人、劉半農(nóng)、楊昌濟(jì)、程演生、劉叔雅、高一涵、李大釗、王星拱等《新青年》雜志的重要作者進(jìn)入北大。陳獨(dú)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如錢玄同、沈尹默、陶孟和、陳大齊等人成為《新青年》作者,實(shí)現(xiàn)了新文化力量的大結(jié)集。從此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形成了集團(tuán)性的力量[⑧],并在北大學(xué)生群里發(fā)揮了深遠(yuǎn)的影響。
在學(xué)生方面,蔡元培大力“扶植社團(tuán)”,倡導(dǎo)學(xué)生組成具有積極意義的社團(tuán),并指派教員進(jìn)行指導(dǎo),開展各種有益的活動(dòng),把學(xué)生的課余興趣吸引到學(xué)術(shù)研究和健康的文體活動(dòng)上來。
隨著北大文科、校部和圖書館相繼搬入紅樓,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諸子們的活動(dòng)場(chǎng)所也逐漸從馬神廟轉(zhuǎn)移到漢花園,北大紅樓在真正意義上成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大本營(yíng),紅樓每個(gè)角落都可以追蹤到他們的足跡。除教員在這里上課,學(xué)生在這里聽講外,不少人在紅樓辦公。蔡元培的校長(zhǎng)室、“我國(guó)白話文的開山老祖”《白話日?qǐng)?bào)》的創(chuàng)辦人李辛白的庶務(wù)主任室都在紅樓二層,陳獨(dú)秀的文科學(xué)長(zhǎng)室也位于紅樓二層,1918年11月,《每周評(píng)論》就在這里誕生。[⑨]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位于紅樓一層的東南角,《新青年》同人常常在這里聚會(huì),[⑩]學(xué)生們也喜歡這里,是師生間“互相問難”、掊擊“舊社會(huì)制度和舊思想”的好地方,從而醞釀出五四新文化期間最有影響的學(xué)生雜志《新潮》[11]。
蔡元培校長(zhǎng)對(duì)各種社團(tuán)都予以大力支持,除親自參加社團(tuán)活動(dòng)外,如出席社團(tuán)會(huì)議,擔(dān)任名譽(yù)會(huì)長(zhǎng),還設(shè)法為社團(tuán)活動(dòng)提供場(chǎng)所,紅樓建成后就成為北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活動(dòng)的重要場(chǎng)所。
1918年11月,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創(chuàng)辦了新潮雜志社,編輯出版具備“批評(píng)的精神、科學(xué)的主義、革新的文詞”三要素的《新潮》雜志[12],大力鼓吹新思想和文學(xué)革命,《新潮》就誕生在紅樓一層二十二號(hào)。
以“昌明書法,陶養(yǎng)性情”為宗旨的書法研究社是由羅常培、俞士鎮(zhèn)、薛祥綏、楊湜生等學(xué)生發(fā)起,1917年12月21日成立,其主要活動(dòng)為“每周任寫各體書呈教員評(píng)定”。書法社的成立得到了蔡元培校長(zhǎng)的大力支持,他請(qǐng)來對(duì)書法頗有研究的文科教授馬衡、沈尹默、劉季平做書法研究社的導(dǎo)師。[13]1918年12月,書法研究社覓定紅樓一層第十三號(hào)為社址,并于社址內(nèi)陳列各種碑帖,供社員臨摹欣賞。其社員廖書倉(cāng)寫的一手好字,也是蔡元培先生發(fā)起成立的當(dāng)年北大又一著名社團(tuán)――“進(jìn)德會(huì)”的會(huì)員。1919年3月,他與鄧康(鄧中夏)一起發(fā)起成立北京大學(xué)平民教育講演團(tuán),并當(dāng)選為總務(wù)干事。[14]
1919年1月,哲學(xué)研究會(huì)在紅樓四層第四教室召開成立大會(huì),以陶孟和、陳大齊為指導(dǎo)教師,并以設(shè)于紅樓四層的哲學(xué)門研究所為社址[15],其主要活動(dòng)為討論哲學(xué)問題,討論會(huì)每月一次公開演講。
1919年1月26日,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北大學(xué)生陳鐘凡、張煊等數(shù)十人,在劉師培家里開會(huì),“慨然于國(guó)學(xué)淪夷’,成立國(guó)故月刊社。這年2月,國(guó)故月刊社覓定紅樓三層三十三號(hào)為社址,接收該社編輯、社員函件、稿件[16]。3月20日,《國(guó)故》月刊出版,成為與《新潮》、《國(guó)民》并列的北大三大學(xué)生刊物。
北大新聞學(xué)會(huì)是中國(guó)第一個(gè)有組織的新聞學(xué)研究團(tuán)體,成立于1918年10月。1919年2月19日,新聞研究會(huì)在紅樓二層西的第34教室召開改組大會(huì),修改、通過簡(jiǎn)章,更名為“北京大學(xué)新聞學(xué)研究會(huì)”,并改選了職員。蔡元培親臨會(huì)場(chǎng)并當(dāng)選為正會(huì)長(zhǎng),徐寶璜當(dāng)選為副會(huì)長(zhǎng),黃杰、陳公博當(dāng)選為干事。此次大會(huì)到會(huì)會(huì)員有毛澤東、譚植棠、區(qū)聲白等24人。1919年3月,新聞學(xué)研究會(huì)覓定紅樓二層十二號(hào)為會(huì)所,仍以34教室為研究地點(diǎn)。這年4月16日,新聞學(xué)研究會(huì)在第34教室召開會(huì)議,決定出版《新聞周刊》。
社團(tuán)活動(dòng)豐富了同學(xué)們的課余生活,拉近了學(xué)生與教員的距離,鍛煉了學(xué)生們的能力,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他們成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新的生力軍,并為他們?cè)谌蘸蟪蔀閷W(xué)生運(yùn)動(dòng)中的領(lǐng)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三、見證五四愛國(guó)運(yùn)動(dòng)全進(jìn)程
1919年5月4日,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列強(qiáng)在巴黎和會(huì)上損害中國(guó)主權(quán)、反對(duì)北京政府的賣國(guó)政策的五四愛國(guó)運(yùn)動(dòng)爆發(fā),北大師生是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導(dǎo)者和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紅樓和她北面的操場(chǎng)是這場(chǎng)愛國(guó)運(yùn)動(dòng)的主要活動(dòng)場(chǎng)所,在此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力促進(jìn)了五四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紅樓從而成為五四運(yùn)動(dòng)最重要的歷史見證,是我們追尋五四運(yùn)動(dòng)當(dāng)事人音容笑貌的最好媒介。
1、《北京全體學(xué)界通告》的誕生地
五四當(dāng)天散發(fā)的《北京全體學(xué)界通告》就是在紅樓誕生的。1919年5月3日,中國(guó)外交失敗的消息從巴黎和會(huì)傳來,群情激憤,北大學(xué)生當(dāng)晚與各高校學(xué)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huì),決定把原定于5月7日國(guó)恥日舉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日,并且當(dāng)場(chǎng)在北大學(xué)生中推出二十名委員負(fù)責(zé)召集,新潮社社員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17]。據(jù)羅家倫回憶,5月4日上午10時(shí),羅家倫從城外高等師范學(xué)校回到位于紅樓一層的新潮社,“同學(xué)狄福鼎(君武)[18]推門進(jìn)來,說是今天的運(yùn)動(dòng),不可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xué)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學(xué)命我執(zhí)筆。我見時(shí)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著靠在一張長(zhǎng)桌旁邊[19]”寫成《北京全體學(xué)界通告》。宣言內(nèi)容如下:
現(xiàn)在日本在萬(wàn)國(guó)和會(huì)要求吞并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quán)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shì)一去,就是破壞中國(guó)的領(lǐng)土!中國(guó)的領(lǐng)土破壞,中國(guó)就亡了!所以我們學(xué)界今天排隊(duì)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guó)出來維持公理。務(wù)望全國(guó)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shè)法開國(guó)民大會(huì),外爭(zhēng)主權(quán),內(nèi)除國(guó)賊。中國(guó)存亡,就在此一舉了!
今與全國(guó)同胞立兩個(gè)信條道:
中國(guó)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guó)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guó)亡了!同胞起來呀![20]
這篇宣言只有一百多字,用的是極簡(jiǎn)潔的白話文,但慷慨激昂,極具號(hào)召力,尤其是“中國(guó)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guó)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兩句,現(xiàn)在讀起來也讓人熱血沸騰,充分反映了文學(xué)革命的成果。羅家倫后來說,他起草這篇宣言時(shí),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wàn)分緊張,但注意力卻非常集中,雖然社里來來往往,很是嘈雜,他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后也沒修改過。[21]這與羅家倫平常白話文寫作的訓(xùn)練是分不開的。宣言寫成后,羅家倫交由狄福鼎送到李辛白所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
到當(dāng)天下午一點(diǎn),北京大學(xué)和其他在京高校學(xué)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集會(huì)時(shí),《北京全體學(xué)界通告》已印成二萬(wàn)份,在集會(huì)和隨后的游行示威中,同學(xué)們把《通告》傳單散分給市民。由于《通告》文字淺白、陳辭懇切,喚起人們心中積怨已久的國(guó)仇家恨,迅速流傳開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五四當(dāng)天唯一的印刷品,對(duì)學(xué)生爭(zhēng)取到市民的支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五四游行的起點(diǎn)
5月4日上午十一時(shí)左右,北大學(xué)生在紅樓后面的操場(chǎng)集合排隊(duì)。這時(shí)教育部派了一個(gè)職員隨同幾個(gè)軍警長(zhǎng)官,勸告他們不要參加游行,學(xué)生們與其理論多時(shí),然后才浩浩蕩蕩走出學(xué)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門行進(jìn),但由于耽擱了一些時(shí)間,等到北大學(xué)生趕到天安門的時(shí)候,其他學(xué)校的學(xué)生都已經(jīng)先到了。
3、迎接被捕獲釋同學(xué)勝利歸來
同學(xué)們?cè)谔彀查T短暫集會(huì)后,游行隊(duì)伍由天安門南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各國(guó)公使館前進(jìn),準(zhǔn)備通過使館區(qū),但遭到了軍警的阻攔,憤怒的學(xué)生轉(zhuǎn)而轉(zhuǎn)向趙家樓曹汝霖宅,火燒趙家樓,并痛打親日派官僚章宗祥。起火之后,大批軍警前來鎮(zhèn)壓,當(dāng)場(chǎng)逮捕學(xué)生32人,其中北大學(xué)生20人。學(xué)生被捕以后,5日上午,北京專科以上學(xué)校的學(xué)生舉行總罷課,通電全國(guó)表示抗議。5日下午蔡元培召集北京14所大專學(xué)校校長(zhǎng)在北京大學(xué)舉行校長(zhǎng)會(huì)議,決定向當(dāng)局提出要求,如果不允許將被捕的學(xué)生全部保釋出來,各校長(zhǎng)就聯(lián)名辭職。其他社會(huì)各界也紛紛電請(qǐng)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xué)生。在巨大的社會(huì)輿論壓力下,北京政府終于同意在5月7日這天釋放被捕學(xué)生。
5月7日上午,北京各高校備汽車前往警察廳,迎接被捕獲釋的同學(xué)。10時(shí)左右,一齊到達(dá)北大,然后各自回歸本校。蔡元培校長(zhǎng)和北大全體師生齊集紅樓門外,迎接被捕同學(xué)返校。當(dāng)師生們見到被捕同學(xué)們的時(shí)候,雙方都非常激動(dòng),有記者是這樣記載這一幕的:“彼此初一見,那一種喜歡不盡的樣子,自然教我難以描寫,尤有那喜歡沒完,將一執(zhí)手,彼此又全都大哭起來,感慨激昂,靜悄悄欲語(yǔ)無言的樣子。”[22]
如此四五分鐘,才由蔡校長(zhǎng)把被捕同學(xué)領(lǐng)到紅樓北面的操場(chǎng)上,同學(xué)們分別站在事先準(zhǔn)備好的五張方桌上和大家見面,所有人還是非常激動(dòng),由于情緒緊張萬(wàn)分,被捕同學(xué)沒有一人說話,在校同學(xué)也沒有一人說話。當(dāng)時(shí)大家只是用熱淚交流。[23]等大家的心情平復(fù)些了以后,蔡元培校長(zhǎng)又召集同學(xué)在操場(chǎng)上訓(xùn)話,據(jù)上海《國(guó)民日?qǐng)?bào)》的記載,蔡元培的訓(xùn)話內(nèi)容大概是:
“諸君今日于精神上,身體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當(dāng)略為休息,況且今日又是國(guó)恥日,何必就急急的上課!諸君或者疑我不諒人情,實(shí)則此次舉動(dòng),我居間有無數(shù)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諸君稍為原諒,自己略受些委曲。并且還望諸君以后……堅(jiān)持冷靜態(tài)度……云云。”[24]
從蔡元培的訓(xùn)話中不難看出,勸學(xué)生們“略為休息”,是對(duì)學(xué)生入獄、游行奔波辛苦的體諒,反映出蔡元培對(duì)學(xué)生的關(guān)心及對(duì)其愛國(guó)熱情的同情;“諸君或者疑為不諒人情”句,可能是蔡元培曾受到過學(xué)生方面壓力,但介于政府與學(xué)生之間的他,難免有力不從心的地方;“望諸君堅(jiān)持冷靜態(tài)度”句,蔡元培還是希望同學(xué)們可以安心讀書專研學(xué)術(shù),不希望他們?yōu)榫葒?guó)運(yùn)動(dòng)而犧牲學(xué)業(yè)。
4、挽蔡斗爭(zhēng)的中心
雖然經(jīng)過師生們的共同努力,被捕同學(xué)被釋放,但北京政府拒絕接受曹汝霖和陸宗輿的辭職,教育總長(zhǎng)和各大專學(xué)校校長(zhǎng)都被軍閥和舊官僚所嚴(yán)厲抨擊,北京大學(xué)更是處在斗爭(zhēng)的中心,內(nèi)閣甚至考慮要解除蔡元培的校長(zhǎng)職務(wù),蔡元培于5月8日晚上收到他被解職,由馬其昶接替的通知。于是他留下兩封辭職信,5月9日清晨秘密離開了北京。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名望本已無人能比,四處奔走營(yíng)救學(xué)生的行為使他獲得了更多的尊敬。
當(dāng)晚8時(shí),北大教職員開全體會(huì),做出“如蔡不留,即一致總辭職”的決議,并推舉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等8人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11日,為進(jìn)行挽蔡斗爭(zhēng),北京各校教職聯(lián)合會(huì)正式成立,北京大學(xué)以紅樓二層一個(gè)房間作為教職員聯(lián)合會(huì)辦事室。[25]
也就是在這個(gè)時(shí)候,那些原本反對(duì)或不支持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教授和學(xué)生也因?yàn)橥觳踢@個(gè)共同的目標(biāo)加入到運(yùn)動(dòng)中來。6月5日,北大教授在紅樓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里開臨時(shí)會(huì)議,討論通過什么方式挽留蔡元培,據(jù)周作人回憶:“各人照例說了好些話,反正對(duì)于挽留是沒有什么異議的,問題只是怎么辦,打電報(bào)呢,還是派代表南下。辜鴻銘也走上講臺(tái),贊成挽留校長(zhǎng),卻有他自己的特別理由,他說道:‘校長(zhǎng)是我們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們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yàn)樗琴澇赏炝舨绦iL(zhǎng)的,所以也沒有人再來和他抬杠。”[26]
學(xué)生們也堅(jiān)決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絕北京政府另派校長(zhǎng)。北京政府繼續(xù)采取了強(qiáng)硬的態(tài)度,命令用軍力來鎮(zhèn)壓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迫使同情學(xué)生的教育總長(zhǎng)傅增湘辭職,政府與教育界的戰(zhàn)爭(zhēng)進(jìn)一步升級(jí)。
5、被武裝軍警包圍
5月19日,北京18所大專學(xué)校的學(xué)生進(jìn)行全體大罷課,要求總統(tǒng)拒簽和約、懲辦賣國(guó)賊曹、章、陸三人、挽留傅總長(zhǎng)、蔡校長(zhǎng)。罷課期間,學(xué)生組織講演團(tuán)四處演講,向市民講述當(dāng)前形勢(shì),并大力提倡購(gòu)買國(guó)貨,號(hào)召市民抵制日貨。5月13日,北大學(xué)生便將該校消費(fèi)公社儲(chǔ)存的日貨,集中在紅樓北面大操場(chǎng)中焚毀。[27]
在日本政府的壓力和親日派官員的影響下,北京政府對(duì)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開展了更大規(guī)模的鎮(zhèn)壓活動(dòng)。6月1日,總統(tǒng)徐世昌頒布兩道命令,第一道稱贊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說他們?yōu)槊駠?guó)立下不少功勞,第二道歸罪學(xué)生糾眾滋事,擾亂公安,告誡他們立刻回去上課。6月3日,軍警開始大規(guī)模逮捕學(xué)生,到下午就逮捕了400余人,由于拘留所無法容納,竟把北河沿北京大學(xué)法科的大房屋變成臨時(shí)學(xué)生拘留所,大門前貼上“第一學(xué)生拘留所”字條。校舍四周,由保安隊(duì)等支棚二十個(gè)露宿監(jiān)視,斷絕交通。到6月4日,局勢(shì)更加緊張,政府竟囚禁了大約1150名學(xué)生。馬神廟北京大學(xué)理科的房屋,已經(jīng)成了第二臨時(shí)拘留所。堂堂最高學(xué)府,竟成了囚禁學(xué)生的地方!!相較之下,紅樓倒是北大校舍中最自由安全的,僅被武裝軍警包圍,“駐兵五棚”。[28]
6、等待蔡校長(zhǎng)歸來
北京政府的這種高壓手段引起全國(guó)各地的憤怒。北京專門以上學(xué)校教職員通電全國(guó),抗議大學(xué)教育的尊嚴(yán)為軍警所破壞。北京專門以上學(xué)校教職員在4日的通電中說:“等學(xué)生于匪徒,以校舍為囹圄,蹂躪教育,破壞司法,國(guó)家前途,何堪設(shè)想!”[29]從6月5日開始,上海將近二十萬(wàn)工人為支持學(xué)生舉行大罷工,隨后幾天南京、蘇州、杭州、武漢等全國(guó)許多城市都卷入罷市風(fēng)潮,鐵路工人也開始罷工。終于,北京政府撐不下去了,6月10日下令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辭職。6月28日,巴黎和約簽字的那一天,中國(guó)代表團(tuán)拒絕在對(duì)德和約上簽字,并向總統(tǒng)提出全體辭職。
7月22日,全國(guó)學(xué)生聯(lián)合會(huì)發(fā)布《終止罷課宣言》,宣告終止罷課。7月23日,蔡元培發(fā)表《告北大學(xué)生暨全國(guó)學(xué)生書》,信中充分肯定了學(xué)生五四救國(guó)運(yùn)動(dòng)的意義,認(rèn)為學(xué)生“喚醒國(guó)民之任務(wù),至矣盡矣,無以復(fù)加矣”,同時(shí)著重指出學(xué)生得受高等教育之不易,要求學(xué)生應(yīng)仍以“研究學(xué)問為第一責(zé)任”,“盡瘁學(xué)術(shù),使大學(xué)為最高文化中心”[30],并答應(yīng)回北京重任北大校長(zhǎng)。蔡元培9月12日回到北京,9月20日正式到北大視事。
1919年9月20日上午九時(shí),北大全體學(xué)生及教職員在法科大禮堂舉行歡迎蔡校長(zhǎng)回校大會(huì)。學(xué)生先到就位,秩序井然。校長(zhǎng)就席后,全體學(xué)生齊刷刷起立向蔡校長(zhǎng)致敬。此于距離蔡元培出走,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四個(gè)多月,大家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大會(huì)由張國(guó)燾主持,由北京學(xué)生聯(lián)合會(huì)、全國(guó)學(xué)生聯(lián)合會(huì)首任主席方豪致長(zhǎng)篇?dú)g迎詞,情真意切地向校長(zhǎng)表明,北大是多么需要他。“回憶(先生)返里之日,人爭(zhēng)走相問曰‘蔡校長(zhǎng)返校乎?’生等嘆大學(xué)前途,每悲不能答”,并誠(chéng)摯地向蔡校長(zhǎng)表明,學(xué)生們對(duì)校長(zhǎng)“訓(xùn)學(xué)生以力學(xué)報(bào)國(guó)”是非常贊同的,犧牲研究學(xué)術(shù)之光陰從事愛國(guó)運(yùn)動(dòng)是“感于國(guó)難”,是不得不為之舉。如今運(yùn)動(dòng)結(jié)束,愿“破除一切頑固思想,浮囂習(xí)氣,以創(chuàng)造國(guó)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學(xué)新紀(jì)元。”[31]
至此,五四運(yùn)動(dòng)中學(xué)生提出的要求全部實(shí)現(xiàn),五四運(yùn)動(dòng)圓滿勝利。
紅樓見證了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蓬勃發(fā)展,見證了北大學(xué)子的拳拳愛國(guó)之心,見證了蔡元培校長(zhǎng)謙沖和藹背后的堅(jiān)毅風(fēng)骨,紅樓從此名揚(yáng)天下。隨著五四運(yùn)動(dòng)的不斷擴(kuò)大,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影響迅速波及全國(guó),紅樓逐漸成為“進(jìn)步、民主”的象征,成為萬(wàn)千青年學(xué)子向往的地方。
--------------------------------------------------------------------------------
[①]《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7年12月17日第二版《新建筑記》。
[②]《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8年3月12日第二版《新齋舍之用途》。
[③] 參考北京市東城區(qū)文化委員會(huì)編著《東華圖志 北京東城史跡錄》第597頁(y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④]《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8年9月30日第二版。
[⑤] 胡適在9月27日給母親的信里說“大學(xué)因新屋一時(shí)不能搬好,故須至十月二日始上課。” 見杜春和編《胡適家書》第217頁(y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8年10月14日第二版《圖書館主任布告》。
[⑦]《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8年10月22日第二版《圖書館主任布告》。
[⑧] 參考陳萬(wàn)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3頁(yè),三聯(lián)書店,1997年。
[⑨] 1918年11月27日,陳獨(dú)秀在這間辦公室召集李大釗、周作人、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開會(huì),議定創(chuàng)刊《每周評(píng)論》。會(huì)上“公推陳(獨(dú)秀)負(fù)書記及編輯之責(zé),余人俱任撰述。”《每周評(píng)論》于1918年12月22日創(chuàng)刊,這是份四開四版的小型報(bào)紙,逢周日出版,編輯所就設(shè)在文科學(xué)長(zhǎng)室內(nèi)。
[⑩] 據(jù)周作人回憶,“(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設(shè)在第一層,東頭靠南,……,那時(shí)我們?cè)诩t樓上課,下課后有暇即去訪他,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當(dāng)不少,除二三人時(shí)常見面之外,別的都不容易找,校長(zhǎng)蔡孑民很忙,文科學(xué)長(zhǎng)陳獨(dú)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煩他們……。在第一院即紅樓的,只有圖書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辦公時(shí)間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適宜。”《知堂回想錄》第530頁(y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 據(jù)羅家倫回憶,由于李大釗平素謙虛和藹,待人誠(chéng)懇,又有方便閱讀新書的條件,當(dāng)時(shí)不少教師和學(xué)生都喜歡到圖書館主任室聊天,圖書館被人稱為“飽無堂”,在這個(gè)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jié)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 見羅家倫《蔡元培時(shí)代的北京大學(xué)與五四運(yùn)動(dòng)》臺(tái)灣《傳記文學(xué)》第五十四卷第五期第15頁(yè)。
[1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號(hào)。
[13] 《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8年2月22日第三版《書法研究社報(bào)告》。
[14] 《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9年3月26日第五版。
[15] 《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9年1月28日第三版《哲學(xué)會(huì)開會(huì)志略》。
[16] 《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9年2月22日第二版。
[17]羅家倫《蔡元培時(shí)代的北京大學(xué)與五四運(yùn)動(dòng)》,臺(tái)灣《傳記文學(xué)》第五十四卷第五期第17頁(yè)。
[18] 狄福鼎(1895-1964),字君武,自號(hào)平常老人,江蘇省太倉(cāng)縣婁東鄉(xiāng)人。當(dāng)時(shí)是北大社團(tuán)畫法研究會(huì)、消費(fèi)公社的會(huì)員,有資料說“五四”游行當(dāng)天他曾與羅家倫、段錫朋、許德珩一起美國(guó)使館遞說帖,后為國(guó)民黨要員。
[19]羅家倫《黑云暴雨到明霞》,轉(zhuǎn)引自《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30頁(y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20] 《晨報(bào)》1919年5月5日第二版《山東問題中之學(xué)生界行動(dòng)》。
[21] 見周策縱《五四運(yùn)動(dòng)史》第151頁(yè)注釋,岳麓書社,1999年。
[22] 上海《民國(guó)日?qǐng)?bào)》,1919年5月10日:《釋放學(xué)生之經(jīng)過》,轉(zhuǎn)引自彭明《五四運(yùn)動(dòng)史》(修訂本)第294頁(yè),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 見孫伏園《回憶五四當(dāng)年》,《五四運(yùn)動(dòng)回憶錄》第258頁(y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79年。據(jù)孫伏園回憶,被捕同學(xué)隨后“向南走到紅樓的休息室中去了。休息室中除被捕同學(xué)以外,有蔡元培先生,也許還有一、二學(xué)生會(huì)的工作人員。據(jù)說蔡先生當(dāng)時(shí)還削了一個(gè)梨給一位被捕同學(xué)吃呢。”
[24]上海《民國(guó)日?qǐng)?bào)》,1919年5月10日:《釋放學(xué)生之經(jīng)過》,轉(zhuǎn)引自彭明《五四運(yùn)動(dòng)史》(修訂本)第294頁(yè),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每周論文(下)》中回憶當(dāng)時(shí)教職員聯(lián)合會(huì)辦事室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頁(yè)。
[26] 《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一》第542頁(y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7] 轉(zhuǎn)引自彭明《五四運(yùn)動(dòng)史》第309頁(yè),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8] 《知堂回想錄·每周評(píng)論(下)》第435頁(y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9] 《軍警壓迫中的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每周評(píng)論》第二十五號(hào),1919年8月6日。
[30] 《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9年7月23日第四版。
[31] 《學(xué)生歡迎蔡校長(zhǎng)之詞》,《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9年9月20日第二版。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