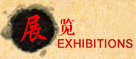北大紅樓,是青年毛澤東新的人生道路的起點。1918年夏和1919年冬,風華正茂的毛澤東兩次來到古都北京,走進不朽的紅樓,與紅樓結下了不解之緣。
1918年8月,為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會同羅學瓚等十二人由長沙前往北京。毛澤東先借居他在湖南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家中,后來在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現(xiàn)名吉安所左巷)七號(現(xiàn)八號),毛澤東與蔡和森、羅學瓚、陳贊周、羅章龍、蕭子升、歐陽玉山、熊光楚八人共同租到一間狹小的普通民房。
為解決生計問題,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到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當上了一名圖書館助理員。在北大,毛澤東雖然是薪資微薄的圖書館助理員,但是他每天到剛剛落成的沙灘紅樓一層西頭靠南三十一號的第二閱覽室即日報閱覽室,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文報紙。這些中外報刊最大限度滿足了他讀報的需求。更何況在紅樓里并不僅僅只有這15種中外報紙。
1918年北大文科大樓(即紅樓)落成,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積推行改革,以近代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為藍本,著手改造封建保守的舊北大。當時北大在校學習的,除正式學生外,還有大量旁聽生,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國最高學府學習的機會對青年毛澤東來說,十分難得。他成了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yè)之發(fā)展為宗旨的新聞學研究會早期積極會員之一。他經常參加研究會的各項活動,每周聽邵飄萍和徐寶璜等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對樂于從事新聞工作的毛澤東來說,這些學習內容都是非常實用的。此外,他還參加了1919年2月19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開的研究會改組大會,他同與會的二十四名會員一起,選舉蔡元培為研究會的會長,徐寶璜為副會長。同時,毛澤東還參加了“哲學研究會”,閱讀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著作,包括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哲學著作。閱讀拓寬了他思維的空間,由于中西方觀念如此之豐富,它們有時候互相支撐,有時候互相駁難,這既使毛澤東迷惑,也為之深深吸引。
在這工作期間,毛澤東一面認真工作,勤奮學習,一面完成此次來京的最初任務——幫助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開展赴法勤工儉學活動。此時北大也設立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蔡元培兼任“華法教育會”會長,積極組織中國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李大釗是積極贊助者之一。毛澤東代表湖南學生和他們商議這方面的事情,同時為幫助湖南學生到留法預備班學習四處奔走。1919年3月,毛澤東送走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儉學學生。
在完成來京任務的同時,毛澤東在北大見到了許多他從各種報刊上看到的新文化運動主將以及風云一時的學生領袖們,如傅斯年、羅家倫等。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這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毛澤東積極尋找機會與這些進步人物接觸,通過與他們交談不斷吸取新的營養(yǎng)。作為毛澤東直接上司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既是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影響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啟蒙者。毛澤東自己就曾說過:“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當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也是指引青年毛澤東不斷前進的導師,早在毛澤東還就讀于湖南長沙第一師范的時候,陳獨秀于1915年創(chuàng)刊的《青年》雜志就深深打動了他。陳獨秀對毛澤東在培養(yǎng)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方面也很有幫助。此外毛澤東主動去拜訪的還有胡適,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毛澤東還和新民學會會員們一起,曾請蔡孑民、陶孟和、胡適之三先生各談話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各問題。當然,這些學者名流對毛澤東等年輕人思想上的影響甚于學術上的影響。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康白情、段錫朋,這些北京大學的師生們,在毛澤東以后的歲月里,有的成了與他同行的同志,有的成了他革命生涯的對手。也是在北大,毛澤東收獲了自己的愛情,愛上了恩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美好的愛情令年輕的毛澤東對生活的困窘視若無睹,他眼里看到的是“北方的早春”,在北海還結著堅冰的時候,他看到的是“潔白的梅花盛開”,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想到了唐朝詩人岑參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
困苦的生活環(huán)境磨礪了他的意志,優(yōu)越的學習環(huán)境增長了他的見識。如果說毛澤東在北大還有什么難以忘懷的,就是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人才濟濟的最高學府,青年毛澤東還是一個不顯眼的小人物,與那些意氣風發(fā)的新文化運動的名人之間,似乎還存在著一道若無實有的鴻溝。他自己也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毛澤東就像是“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魚”。在北大受到的冷遇也許令毛澤東終生難忘,但不影響他在北大埋頭吸取當時先進的知識與思想,更不會影響他對理想的追求,與其他受過教育的中國年輕人一樣,青年毛澤東依然在為中國“找尋出路”。在北大紅樓工作學習一段時間之后,毛澤東覺得自己“對政治的興趣繼續(xù)增長”,而且“思想越來越激進。”雖然在這個時候他的思想還是混亂的,他說:“我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但是他在北大的時期正是五四運動的前夜,新文化運動蓬勃發(fā)展的時期,也是毛澤東的思想將變未變之際。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對他的影響是巨大的,直接啟蒙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信仰。他受陳獨秀的影響很深,因陳是他多年來在文學方面的崇拜對象,又因為陳不妥協(xié)地擁護一切不受束縛的、充滿活力的新興事物,能夠滿足他渴求解放的同一愿望。他在“李大釗手下”向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fā)展,不僅因為李大釗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創(chuàng)始人,毛澤東從李大釗那里擴大了這方面的知識,還因為他同李非常相像,也是滿懷熱情地獻身于使中國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事業(yè)。
青年毛澤東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則是他第二次到北京的時候,1919年底,毛澤東因為湖南省開展的驅張運動再次到北京,雖然沒有在北大校內工作,但他的許多活動卻是在北大校內進行,或是與北大有密切關系。當時“北大公社”成員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辦了一個“亢慕義齋(共產主義小組)”,收藏了許多俄國革命的新書,毛澤東常去那里看書。對此,他回憶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18年9月到1920年4月,毛澤東兩度來京,在北大紅樓度過了半年多的時光,并與北大的進步人士保持聯(lián)系,雖然時間并不長,但是這段經歷對他卻是極為重要的,對年輕的毛澤東來說,在北大紅樓既是向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人物學習,又是對他自己的一種激勵,而對馬克思主義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的認識和接觸更影響了他的一生。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