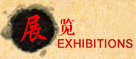歲月長(zhǎng)河中一個(gè)最普通的日子。秋日的陽(yáng)光把中原大地涂抹成夢(mèng)幻般的金黃,李灣水庫(kù)庫(kù)區(qū)帶著有山有水有樹林的溫柔形象,把月臺(tái)附近打扮成江南水鄉(xiāng)。我們一行來(lái)到河南新密牛店鎮(zhèn)月臺(tái)村,和一片再平常不過(guò)的麥田結(jié)下了千古奇緣,這里是河南省新密文物普查隊(duì)新近發(fā)現(xiàn)的一處重要文化遺址——瓷器窯址。
這個(gè)平和寧?kù)o的早晨,甚或能看見(jiàn)晨曦在枝頭蕩漾。陽(yáng)光在廣袤的原野鋪天蓋地,同樣廣袤的時(shí)空里,我看見(jiàn)前賢們行色匆匆步伐。
一位頭戴高冠,腰佩寶劍的千年詞人吟唱: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shí)。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愛(ài)喝菊花酒的陶潛在南山前無(wú)奈地抒發(fā)農(nóng)家樂(lè):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zhǎng),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wú)違。
又有一位起宋代詞人在《揚(yáng)州慢》中向我抒發(fā)的黍離之悲:
過(guò)春風(fēng)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
發(fā)配途中的屈原、辭官不做的淵明、南宋戰(zhàn)亂時(shí)代的姜夔看見(jiàn)黍苗與太平盛世的我看到的麥苗心境多么的不同。相同的是,我和古人同樣站在歷史地長(zhǎng)河,清醒地觀看人類自己的表演,記住時(shí)空及時(shí)空中的人和事如何匆匆從眼前走過(guò)。
動(dòng)蕩的年代,人們有心或無(wú)意破壞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太平盛世,人們想到保護(hù)人類從遠(yuǎn)古時(shí)代就堆積和遺存的文化遺產(chǎn)。
這片豆苗青青的麥地,曾經(jīng)生活著戰(zhàn)亂頻仍的五代人,這個(gè)年代有貴為天子的柴榮,也有貧賤的窯工。連年的戰(zhàn)亂讓輝煌的文明和物質(zhì)銷聲匿跡,而我,幸運(yùn)地生在和平富庶的年代,我們的任務(wù)是讓曾經(jīng)的文明復(fù)原,至少是找到當(dāng)年的文化遺址并力圖保存,讓歷史不能忘懷。我打量這片麥苗,文化厚重感和滄桑感如驚濤駭浪般朝我洶涌而來(lái)。
據(jù)說(shuō)這里是后周世宗柴榮御用官窯____柴窯所在地。如今被河南省文物局暫時(shí)稱為月臺(tái)瓷窯遺址。
月臺(tái)瓷窯遺址中部被月臺(tái)河分割,河兩岸分布著階梯狀臺(tái)地和溝壑,遺址就分布在月臺(tái)河兩岸及與月臺(tái)河相連的溝壑兩側(cè)。
《河南省密縣地名志》載:“月臺(tái):月臺(tái)村委會(huì)駐地。在牛店鄉(xiāng)人民政府駐地南6.9公里,與登封縣交界處。相傳,北宋皇帝趙匡胤前往中岳廟進(jìn)香時(shí),曾在此夜宿,到村西土崗臺(tái)地上賞月,因名月臺(tái)。”
明代洪武時(shí)曹昭所著《格古要論•古窯器論》記載:“柴窯器,出北地河南鄭州。世傳周世宗柴氏時(shí)所燒者,故謂之柴窯。天色青,滋潤(rùn)細(xì)膩,有細(xì)紋,多是粗黃土足,近世少見(jiàn)。”
《陶雅》說(shuō):“柴窯出河南鄭州。”《陶雅》亦稱:“后周都汴,唐屬河南道……柴窯,當(dāng)即在其都內(nèi)。”
柴窯是五代名窯,位列宋代五大名窯“鈞、汝、官、哥、定”之前,為諸窯之冠 。柴窯具有的五個(gè)特征“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令本來(lái)就十分稀少的柴瓷價(jià)值連城,素來(lái)有“片柴值千金”的說(shuō)法。如此名貴的窯址又怎么成為歷史的廢墟了呢?
有一種說(shuō)法或可稱為一種詮釋:“杯酒釋兵權(quán)”的宋太祖趙匡胤深知連年的戰(zhàn)爭(zhēng)導(dǎo)致社會(huì)貧困,影響政權(quán)穩(wěn)定,他批評(píng)魏國(guó)長(zhǎng)公主棉襖上裝飾翡翠珠寶;打碎后蜀孟昶裝飾七寶的小便器并喃喃自語(yǔ):你小便器上裝飾七寶,那你吃飯的容器上該用什么裝飾?如此嬌奢淫欲,不滅亡才怪呢!為了最大可能恢復(fù)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增加社會(huì)財(cái)富,讓疲憊不堪的百姓休養(yǎng)生息,下令關(guān)閉了這座盛極一時(shí)的御用官窯。從此柴窯銷聲匿跡 ,甚至具體窯址都無(wú)法準(zhǔn)確辨認(rèn)。
當(dāng)年金戈鐵馬、戎馬生涯、文功武治、政績(jī)不菲的柴世宗哪里又會(huì)想到,柴窯消失在自己義弟一聲令下。人聲鼎沸、爐火通明換得如今西風(fēng)殘照,風(fēng)光不再。
我找到幾片瓷器碎片,仔細(xì)打量,發(fā)現(xiàn)樣品無(wú)論是白瓷還是青瓷,均質(zhì)地輕薄,器表十分光滑,有些有開(kāi)片,倒是符合傳說(shuō)中的柴窯的五大特征。
站到麥地高處,四周安靜得可以聽(tīng)見(jiàn)自己的心跳,時(shí)光依舊按照自己的步伐 從容走自己的路,卻把許許多多的人和事拋棄在自己的后面,任憑如何追趕也是徒勞。
有風(fēng)從亙古吹來(lái),似乎聽(tīng)到古代窯工的歌聲以及勞作時(shí)發(fā)出的巨大聲響,我知道,這不是幻覺(jué),而是歷史的回響:遠(yuǎn)古的歲月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后來(lái)者敘述自己的故事。
假如歲月真的復(fù)活,我會(huì)執(zhí)著的反復(fù)詢問(wèn):這片沉睡的莊稼地真的是曾經(jīng)的柴窯嗎?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