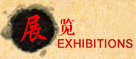張杰
蕭振鳴著《魯迅美術(shù)年譜》,是在魯迅研究厚重的歷史和豐碩成果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這一學(xué)術(shù)背景,為此類研究提供了至少兩個前提:一、可資借鑒的資料和文獻十分豐富,二、遺留的學(xué)術(shù)空間卻未必廣闊。
魯迅研究系當(dāng)今顯學(xué)之一,僅《魯迅年譜》在上世紀(jì)七、八十年代就出版達五、六種之多。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在名人年譜的出版史上絕無僅有,所產(chǎn)生的成果也呈一時之盛,并迅速豐富和深刻地影響了此后的魯迅研究。與這種情況相伴隨,作為魯迅研究重要分支的魯迅美術(shù)活動研究,在近二、三十年中也有長足的發(fā)展,成果同樣豐碩。當(dāng)《魯迅美術(shù)年譜》新書到手,疑問也隨之產(chǎn)生:在如此狹小的施展空間中,此書除冷飯重炒和集資料之大成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價值?在閱讀此書之后,上述問題不僅一掃而空,而且還不禁為此書的諸多長處擊節(jié)叫好。
《魯迅美術(shù)年譜》雖然是專題性年譜,卻是一部在專題范圍內(nèi)十分全面和極具開拓型的年譜。先說全面。熟悉魯迅生平業(yè)績的讀者知道,魯迅的美術(shù)活動,主要在提倡新興版畫方面,卻不以此為限。但是其“限”在何處?在讀者的心目中是不同的,學(xué)界也未予深入的探討和界定。《魯迅美術(shù)年譜》的作者在注重厘清“美術(shù)”這一概念的同時,根據(jù)歷史和魯迅兩方面的特征,極力但也是實事求是地拓展了“美術(shù)”的外延,其具體的實踐正如《出版說明》所聲言:
“美術(shù)” 一詞始見于歐洲17世紀(jì),泛指具有美學(xué)意義的建筑、繪畫、雕刻、文學(xué)、音樂等。近代日本以漢字意譯,“五四”運動前后傳入中國,開始廣泛應(yīng)用。1913年,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發(fā)表的《擬播布美術(shù)意見書》一文中闡述了魯迅的美術(shù)觀,并指出美術(shù)的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又說:“美術(shù)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謂。茍合于此,則無間外狀若何,咸得謂之美術(shù);如雕塑,繪畫,文章,建筑,音樂皆是也。”即通過美術(shù)家的思維活動美化客觀事物都稱為美術(shù)。這里魯迅所說的“美術(shù)”即指廣義美術(shù),即現(xiàn)用的“藝術(shù)”一詞。本譜延用魯迅關(guān)于“美術(shù)”一詞的闡釋,凡有關(guān)建筑、考古、碑拓、雕塑、書法、繪畫、書籍裝幀、書法、雕版諸項均收入年譜中。凡魯迅所論美術(shù)文章、演講、書信均按首發(fā)時間選錄或作提要收入本譜。
在這樣開闊的視野之下,《魯迅美術(shù)年譜》對魯迅美術(shù)活動的成就的觀照就呈現(xiàn)了以下狀態(tài):
魯迅一生的美術(shù)成就大致如下:
收藏原拓中國現(xiàn)代版畫2000多幅、原拓外國版畫2000多幅、碑拓及漢畫像6000多件;
收藏中外藝術(shù)書刊600多種;
最早紹介外國美術(shù)在中國刊物上發(fā)表;
創(chuàng)辦“木刻講習(xí)班”,培養(yǎng)了中國第一代現(xiàn)代版畫家;
舉辦多次版畫展覽;
支持和指導(dǎo)10余個美術(shù)社團;
編輯出版中外美術(shù)書刊10余種;
發(fā)表大量論中外美術(shù)的文章;
翻譯多種國外藝術(shù)理論書籍和論文;
留下巨量手稿的書法墨跡。
我以為,將魯迅的美術(shù)活動和成就,如此搜羅無遺,如此全面完整地納入研究范圍,是《魯迅美術(shù)年譜》對魯迅研究的一大貢獻。
再說開拓。事實上前面所說的全面,已經(jīng)包含了開拓的內(nèi)容,只不過有些內(nèi)容是隱性的,未能顯出明顯的開拓步伐罷了。而顯性的開拓,跨度則十分顯著。例如,作者提到的魯迅收藏的碑拓和漢畫像6000多件,原本屬于金石學(xué)(即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xué))研究。是蔡元培最早發(fā)現(xiàn)了魯迅搜集和整理古碑拓的獨特視角和美術(shù)價值。他指出:“金石學(xué)為自宋以來較發(fā)展之學(xué),而未有注意于漢碑之圖案者,魯迅先生獨注意于此材料之搜羅;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紀(jì)程》,《北平箋譜》等等,均為舊時代的考據(jù)家鑒賞家所未曾著手。”(《<魯迅全集>序》)從此魯迅藏漢畫像及其活動引起魯迅美術(shù)活動研究者的重視,并被納入了研究范圍。《魯迅美術(shù)年譜》將蔡元培指出的這一路徑訴諸實踐和發(fā)揚光大,尤其可貴的是將這一領(lǐng)域的所有內(nèi)容均加以細(xì)化,使之一一落到實處,落實到特定的時空之內(nèi)。這種作法在魯迅研究中尚屬首次。
如果說將魯迅的金石學(xué)研究從美術(shù)角度加以觀照,是受到蔡元培的啟發(fā)和引領(lǐng)的話;那么,將魯迅藏碑拓納入書法藝術(shù)研究,在幾十年的魯迅研究中,《魯迅美術(shù)年譜》則是首創(chuàng)。魯迅所藏碑拓,如果作非專業(yè)的劃分,最簡單的可分為文字和繪畫圖案兩種,而以文字形式者居多,其中又不乏歷代的名碑和精品。有些名碑,除了它的文獻價值、歷史價值之外,在中國書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國書法史上盡管這些名碑的地位自在,然而在幾十年來的魯迅研究中,這些名碑的“魯迅收藏”和“魯迅整理”的因素卻被長期忽視,魯迅極為富有的碑拓收藏和精心勞作,極少出現(xiàn)在魯迅美術(shù)活動研究中。而《魯迅美術(shù)年譜》則一舉扭轉(zhuǎn)了這一局面,并因此進一步豐富了魯迅研究。
魯迅是一個“縱貫古今,橫跨歐亞”的文化巨人。他在美術(shù)領(lǐng)域的活動和成果同樣是這樣。《魯迅美術(shù)年譜》在魯迅異域美術(shù)的譯介方面所作的研究,同樣給予了極高的重視,并且為突出年譜的性質(zhì)和特點,作了巧妙的安排。如果比較深入地理解魯迅,可知1924年與1925年之交,是魯迅在藝術(shù)方面視角轉(zhuǎn)移的重要時段,這種轉(zhuǎn)移既涉及古今,也涉及中外。為說明這一轉(zhuǎn)移,《魯迅美術(shù)年譜》對1925年初魯迅的購書作了較為突出的安排。例如,對魯迅在2月3日所購英文《羅丹之藝術(shù)》,3月5日所購的日文《新俄美術(shù)大觀》、《現(xiàn)代法蘭西文藝叢書》六本、《藝術(shù)的本質(zhì)》等,不僅一一入譜,還另加說明。尤其令入意外的是,年譜還在此處對銷售日文書籍的東亞公司,順便作了介紹。對魯迅購書而言,在北京時期的東亞公司,猶如上海時期的內(nèi)山書店,重要性無以倫比,而前者恰恰為許多魯迅研究者所忽視。《魯迅美術(shù)年譜》這種從心細(xì)如發(fā)的細(xì)節(jié)中所體現(xiàn)的大局觀,令人不得不對它刮目相看。
《魯迅美術(shù)年譜》以鉤沉全部可靠的魯迅與美術(shù)的史料為基礎(chǔ),是近年來學(xué)術(shù)著作中少有水分的“干貨”,從而可以看出著者多年的嘔心瀝血。這本書從封面提字到封底設(shè)計、從前言到后記均為著者一人所為。這是一個老魯迅博物館人難能可貴之處。
總之,《魯迅美術(shù)年譜》是一本值得向讀者推薦的好書,它的厚重、精細(xì)、學(xué)術(shù)性和可讀性,都說明了這一點。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