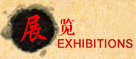陳平原
首先,祝賀“魯迅的讀書(shū)生活”專題展在北大百年紀(jì)年講堂舉辦,此舉將使北大師生更加接近魯迅的日常生活、學(xué)術(shù)趣味以及精神境界。關(guān)于魯迅著作的意義、魯迅的讀書(shū)經(jīng)驗(yàn),魯迅與北大的歷史聯(lián)系等,學(xué)界早有論述,無(wú)須我贅言。請(qǐng)?jiān)试S繞個(gè)彎子,談?wù)勎沂窃趺唇咏斞傅摹?br />
明年是王瑤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此前,我們已出版了七卷本的《王瑤文集》(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八卷本的《王瑤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另外,還有三本紀(jì)念或研究文集。今年,為了便于閱讀,北大出版社推出“王瑤著作系列”,包括《中古文學(xué)史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論集》和《中國(guó)文學(xué):古代與現(xiàn)代》。第三種是新編的,我將選目發(fā)給幾位王先生的弟子,師兄錢理群建議刪去其中的《魯迅和書(shū)》,說(shuō)這文章專業(yè)性不夠。他說(shuō)的對(duì),我刪了;可還是隱約覺(jué)得有點(diǎn)遺憾。
《魯迅和書(shū)》撰于1983年11月,從未在報(bào)刊上發(fā)表,直接收入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魯迅作品論集》。此文專談魯迅的“愛(ài)書(shū)成癖”——“像魯迅這樣愛(ài)書(shū)成癖的習(xí)慣,正是從一個(gè)側(cè)面表現(xiàn)了魯迅對(duì)于知識(shí)和真理的執(zhí)著追求的精神。”接下來(lái)大談愛(ài)書(shū)與愛(ài)國(guó)、博與專、比較與鑒別、觀察與思考等。文章的焦點(diǎn)有些漂移,大概是怕被誤解,將魯迅說(shuō)成“書(shū)呆子”,因此趕緊補(bǔ)充:“他在讀書(shū)的同時(shí),始終把社會(huì)實(shí)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這正顯示了魯迅的戰(zhàn)士與學(xué)者統(tǒng)一的本色。”在我看來(lái),所謂“愛(ài)書(shū)成癖”,本身是一種“文人氣”,沒(méi)什么好忌諱的。
日本平凡社1994年出版了荒井健編的《中華文人の生活》,最后一章是中島長(zhǎng)文撰寫(xiě)的《魯迅における“文人”性》,指出魯迅是戰(zhàn)士,是學(xué)者,是思想家,但也有“文人趣味”。比如花木興味、筆墨情趣、購(gòu)書(shū)籍、藏拓片、編箋譜、賞繡像,還有鈔古書(shū)、自稱“毛邊黨”等,都不是為了完成某個(gè)學(xué)術(shù)課題,而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故沉湎其中。在這一點(diǎn)上,主張“不讀或少讀中國(guó)書(shū)”的魯迅,有其“書(shū)生本色”。
我之接近魯迅,跟一般人不太一樣,除了思想與文學(xué),還有物質(zhì)形態(tài)的“書(shū)籍”作為媒介。這方面,我主要得益于兩本書(shū):一是唐弢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書(shū)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83),此書(shū)收錄了諸多專家所撰關(guān)于魯迅著作版本流變的文章,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魯迅接受史”。另一本則是上海魯迅紀(jì)念館和中國(guó)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上海分會(huì)合編的《魯迅與書(shū)籍裝幀》(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1),此書(shū)除了印刷精美,可供把玩,書(shū)前錢君匋的《序》以及編者輯錄的《魯迅論書(shū)籍裝幀》,都很有用。
再說(shuō)開(kāi)去。我在中山大學(xué)念碩士時(shí),有三位導(dǎo)師:近代文學(xué)方面我受教于陳則光先生,現(xiàn)代文學(xué)則以吳宏聰先生為主,至于新文學(xué)書(shū)籍以及魯迅著作版本等,這方面的興趣與能力,主要得益于饒鴻競(jìng)先生。饒教授曾任創(chuàng)造社主將、中大黨委書(shū)記馮乃超的秘書(shū),參與注釋魯迅的《而已集》,當(dāng)過(guò)中大圖書(shū)館副館長(zhǎng),編有《創(chuàng)造社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億兆心香薦巨人——魯迅紀(jì)念詩(shī)詞集》(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1986)等。依我的觀察,他有“把玩書(shū)籍”的興趣,每回見(jiàn)面,總是侃侃而談,然后不無(wú)炫耀地亮出某本好書(shū)。八十年代后期,我開(kāi)始出書(shū),他叮囑,凡是論述的,不必送;若是史料或談?wù)摃?shū)籍的,一定要寄來(lái),因?yàn)樗矚g。我知道,現(xiàn)代文學(xué)界有不少像饒先生這樣因“書(shū)籍”而與作家(比如魯迅)結(jié)下深情厚誼的。現(xiàn)在不一樣了,發(fā)表的壓力越來(lái)越大,學(xué)者們只顧寫(xiě)書(shū),而不再愛(ài)書(shū)、藏書(shū)、賞書(shū)、玩書(shū)了,這很可惜。
沒(méi)錯(cuò),魯迅是個(gè)偉大的戰(zhàn)士,可魯迅也是個(gè)普通讀書(shū)人;正因此,不僅可敬,而且可愛(ài)。有機(jī)會(huì)在魯迅博物館的地庫(kù)觀賞魯迅當(dāng)年補(bǔ)鈔的古書(shū),確實(shí)震撼。那次是跟陳丹青一起看,一開(kāi)始,我們倆都認(rèn)為不像手寫(xiě),仔細(xì)辨認(rèn),方才認(rèn)可。關(guān)鍵不在技術(shù),而在心態(tài)。現(xiàn)在談魯迅,更多關(guān)注其“上下求索”與“橫眉冷對(duì)”,很少深究其孜孜不倦、其樂(lè)無(wú)窮的讀書(shū)生活。不就是“讀書(shū)”嗎,太一般了,缺乏戲劇性,不夠偉大。記得魯迅說(shuō)過(guò),“偉大也要有人懂”。某種意義上,任何一個(gè)偉大人物,瞬間爆發(fā)出來(lái)的巨大生命力,是以平淡無(wú)奇的“日積月累”為根基的。
理解魯迅,除了大量著作與譯述,還要看他如何編輯書(shū)刊、收集漢唐畫(huà)像石、輯校古籍、編印《北平箋譜》和《十竹齋箋譜》等。翻看那3函18冊(cè)的《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書(shū)畫(huà)出版社,1986)、6函49冊(cè)的《魯迅輯校古籍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魯迅藏漢畫(huà)像》一、二集(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6、1991年),還有《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9),都讓我們對(duì)魯迅的學(xué)識(shí)與趣味有更深入的了解。魯迅確實(shí)了不起,讀了這么多書(shū),做了這么多事;但某種意義上,這些都是讀書(shū)人的本份。
不知什么時(shí)候起,“讀書(shū)人”這個(gè)本來(lái)很好的詞,被污名化了,變成與“思想家”或“革命者”截然對(duì)立。于是,讀書(shū)必須講效果,書(shū)齋連著戰(zhàn)場(chǎng),否則沒(méi)有意義。魯迅博物館編的《魯迅的讀書(shū)生活》(人民日?qǐng)?bào)出版社,2003),提及魯迅在上海的書(shū)屋:“1933年,魯迅在狄思威路租房一間作藏書(shū)室。”(第86頁(yè))這么寫(xiě)很好,就是一間書(shū)屋,沒(méi)什么“微言大義”。對(duì)于讀書(shū)人來(lái)說(shuō),書(shū)太多,放不下,又舍不得丟,另外租房存放,再正常不過(guò)了。文革中,為了神化魯迅,曾就此大做文章,說(shuō)這間“秘密讀書(shū)室”是專門儲(chǔ)藏馬列著作和革命書(shū)籍,魯迅如何在夜色掩護(hù)下,擺脫了特務(wù)的跟蹤,來(lái)到這苦讀禁書(shū)。當(dāng)然,這些都是虛構(gòu)的。再說(shuō),過(guò)于“目標(biāo)明確”的讀書(shū),其實(shí)不是理想狀態(tài)。
順便提一句,《魯迅的讀書(shū)生活》有個(gè)小錯(cuò)誤,第82頁(yè)兩處提及“章延謙”,應(yīng)該是“章廷謙”,即北大中文系教授川島(1901-1981)。章先生字矛塵,浙江紹興人,與魯迅關(guān)系很密切。第78頁(yè)所載魯迅在廈門的中國(guó)照相館拍的照片,就是題贈(zèng)給他的。你看,上面是魯迅題的“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下面則是“矛塵先生惠存,魯迅”,還鄭重其事地蓋了名章。
這兩年,我先后在北京大學(xué)、香港中文大學(xué)、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xué)做題為“作為一種物質(zhì)文化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專題演講。我以為,親眼目睹、親手觸摸這些作為物質(zhì)形態(tài)的文學(xué)作品,了解其生產(chǎn)與傳播、接受與鑒賞,對(duì)于進(jìn)入歷史,從事專業(yè)研究,十分重要。這方面、圖書(shū)館和博物館有很多工作可做,用時(shí)尚的話,“有很大的拓展空間”。這次魯迅博物館開(kāi)了個(gè)好頭,讓我們得以借助這個(gè)專題展,既讀魯迅的書(shū),也讀魯迅如何讀書(shū),實(shí)在機(jī)會(huì)難得。作為主辦單位之一,我代表北大中文系,既感謝魯迅博物館,也感謝北大百年紀(jì)年講堂,更感謝即將參觀此展覽的無(wú)數(shù)北大師生。
(此文乃作者2008年9月19日在北大百年紀(jì)年講堂舉行的“魯迅的讀書(shū)生活”專題展開(kāi)幕式上的發(fā)言)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