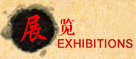陳世崇
我知道汪曾祺的大名是在1980年,我在《北京文學》小說組當編輯,那時主持《北京文學》工作的是李清泉。有一天李清泉開完會后,來小說組轉轉,與編輯聊天,聊到一個叫汪曾祺的人寫的一篇小說。
當時市文聯(lián)雖已與市文化局分開,為平行單位,但上面都歸一個領導主管。那天的會就是這位主管領導召集的,文化局和文聯(lián)的中層以上的領導干部參加,會議的主題是“說說各單位的新動向”。就是在這個會上,有人講到:京劇團的編劇汪曾祺不寫劇本寫小說;寫了小說卻又不拿出去發(fā)表,只是讓周圍的人傳著看看;小說寫的是小和尚談戀愛的事兒。這樣的內容、這樣的方式,在當時有點兒犯忌。參加會的《北京文學》主要負責人(那時主編不叫主編,而沿用“文革”以來的稱謂,叫“編輯部領導小組主要負責人”)李清泉,是延安老“魯藝”的,20世紀40年代他讀過汪曾祺的作品,有印象,出于一個老編輯家的職業(yè)敏感,使他忘卻了政治氣候的“乍暖還寒”,當即對那位同志說:請您把汪曾祺的這篇稿子讓人給我?guī)砗脝?我看看。李清泉看過稿子,如獲至寶,當即簽發(fā),這就是登在《北京文學》1980年10月號上的《受戒》。
《受戒》發(fā)表之后,引起了文壇轟動。在是年底召開的有全國17家主要文學月刊主編參加的一次會議上,《受戒》被公認為當年最優(yōu)秀的一個短篇小說。這位20世紀40年代就出版過作品集的人,似乎此時才被人們發(fā)現(xiàn),一篇《受戒》確立了他小說名家的地位。
汪曾祺一舉成名。各家報刊、出版社約稿者紛至沓來。
但是汪曾祺對《北京文學》情有獨鐘。《受戒》的發(fā)表開啟了汪曾祺和《北京文學》的蜜月期。從那以后到1989年1月,汪曾祺陸續(xù)在《北京文學》上又發(fā)表了8篇小說、11篇散文、1篇創(chuàng)作理論和1篇作品評論。
后來李清泉調《人民文學》主持工作。那時,全國的文學獎評選活動由人民文學雜志社具體操辦,而評委會則聘請冰心、劉白羽、宗璞、王蒙等文壇名家組成。有位特別欣賞《受戒》的評委不無遺憾地問李清泉:“怎么不把《受戒》發(fā)頭條呢?”沒等李清泉作答,另位評委就說:“能發(fā)出來就不容易,就夠有膽識的!”這位評委當時是北京作協(xié)的專業(yè)作家,他了解李清泉主持《北京文學》這塊園地為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沖鋒吶喊、敢為天下先的所作所為。在《受戒》發(fā)表三個月后,李清泉離開了《北京文學》,有人受命來扭轉《北京文學》的方向。授命者,便是主持召開那次中層干部會,讓大家談談各單位“思想新動向”的領導。當然,這些內情并非眾評委人人盡知,但大家對社會氣候冷暖的感知還是相近的。所以,議論歸議論,贊賞歸贊賞,初選小組沒把《受戒》列入備選篇目,評委們也沒人提議把它補進來。大家都心照不宣。
汪曾祺第二年獲獎了,獲獎作品是發(fā)表在《北京文學》1981年4月號上的《大淖記事》。有人說,1980年小說評獎,甭管什么原因,確實虧待了《受戒》、虧待了汪曾祺、虧待了《北京文學》,因此才有了次年《大淖記事》的獲獎,這獎一半兒是給《受戒》的。此屬臆測,不必當真。不過,汪公本人最鐘愛的作品的確是《受戒》而非《大淖記事》。記得20世紀80年代末的一天,我和兩位作家到汪公家去,聊到他的作品譯介國外的情況。那時他的許多作品都譯介到國外去了,而《受戒》卻偏偏是個例外。不是沒人要譯,而是他不讓。問及緣由,回答說:怕譯不好味道全沒了。鐘愛之情可見一斑。
人們都說汪老清高,其實汪老是位很重感情的人。他受知于《北京文學》,對真正懂得文學創(chuàng)作的編輯家李清泉有一種特殊的尊重。自李清泉離開《北京文學》以后的幾年,編輯方針有所變化,刊物在這個時期遇到了一定的困難。1985年,我受命主持《北京文學》全面工作之初,就登門拜訪汪老,向他討教辦刊的思路和辦法。汪老不吝賜教,直截了當地呼吁“魂兮歸來!”魂是什么?汪老說就是李清泉在《北京文學》時的那個路數。李清泉在《北京文學》期間提出的編輯方針:提倡文學作品“真實性、藝術性和思想性的統(tǒng)一”、“在思想健康的前提下,作品的藝術性應受到特別的重視。”在這種編輯思想的指導下,李清泉簽發(fā)了幾家刊物都不敢發(fā)的方之的《內奸》(此文獲1979年全國小說一等獎),以及《愛,是不能忘記的》等等讓人耳目一新、引起文壇震動的一系列作品。《北京文學》一時聲名鵲起,被譽為“全國文壇甲級隊”;不過這在當時為李清泉招來了諸多非議,說他鼓吹“藝術至上”,公開與黨提倡的“思想性第一”唱對臺戲。而汪曾祺則認為:李清泉是一位真正懂得文學的編輯家。直到我向他討教時,他仍然認為,按李清泉提出的路數去辦,就一定能再把刊物辦上去。他自告奮勇說:只要有李清泉出面,他是隨叫隨到;別的作家,比如王蒙呀、鄧友梅呀等等名家,他負責去請。大家聚聚,在一塊兒聊聊,給《北京文學》寫稿。也不用備飯,一杯清茶即可。
1986年初,林斤瀾出任《北京文學》主編。我和他議及汪老的意見,他深表同意。這些意思都溶入后來由斤瀾老執(zhí)筆寫的一個“編者按”里。“編者按”站在刊物的角度,大膽做了反醒,并提出了與“三性”精神相通的四條:1、追求作品的時代性;2、歡迎如《受戒》那樣純情至美的作品;3、提倡像《愛,是不能忘記的》那樣富有個性的探索作品;4、強調作品的可讀性。“編者按”最后坦誠地向廣大作者呼吁“田將蕪兮,胡不歸?”
理清思路,編輯思想明確,堅持幾年,果見成效。1986~1989年,《北京文學》新人佳作迭出:余華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現(xiàn)實一種》,劉恒的代表作《伏羲伏羲》,劉震云的代表作《單位》、劉慶邦的代表作《走窯漢》等等都是這個時期在《北京文學》上面世的。這個時期被稱為《北京文學》的“第二個高峰”,其中汪老的重要貢獻,長期以來卻不為眾人知。
汪老對《北京文學》的關注和支持不止是出謀劃策、把好稿子多給《北京文學》,而且是多方介入,甚至是做一些最基礎的工作。《北京文學》辦的筆會,他是有請必到,和與會者聊創(chuàng)作、談稿子。因了汪老和眾多名家的參與,那時《北京文學》辦的許多筆會,都很有生氣、很有收獲,為許多兄弟刊物所艷羨。
《北京文學》辦的業(yè)余作者創(chuàng)作班到外地面授,請汪老,他也去。20世紀80年代,《北京文學》與北京作家協(xié)會合作舉辦業(yè)余作者創(chuàng)作班,授課形式有函授和面授兩種。1986年4月,創(chuàng)作班在山西大同舉行面授輔導,這次面授的具體組織者是《北京文學》的季恩壽。汪老和《北京文學》副主編李陀也去了。大同的業(yè)余作者曹乃謙參加了這次面授,他把自己的作品《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拿給季恩壽看,季說:“絕好”;拿給李陀看,李說“極好”;拿給汪老看,汪老脫口叫好。李陀說:“希望你寫系列,我?guī)湍愠鰰?rdquo;;汪老說:“若要出書,我給你作序。”面授結束后回到北京,曹乃謙的這篇稿子交到編輯部,一同交來的還有汪老為其寫的長達幾千字的評介文章。這兩篇文章是我簽發(fā)的,發(fā)在1988年6月號《北京文學》的頭、二條。我至所以在這里提起這件事,是因為最近我看到北京兩家報紙上的兩篇寫曹乃謙的文章,兩篇文章都說到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說他有希望得諾獎”;也都提到其成名作《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一篇說《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是在《╳╳文學》發(fā)表的,汪老看后說好;另一篇的說法更有趣,說《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在《北京文學》發(fā)表是曹乃謙與朋友打賭的結果。起因是曹在大同當地的報刊上發(fā)了兩篇文章后,朋友不服氣,說:我看你大同有熟人,有本事在北京、上海來一篇。念及北京比上海近,于是曹乃謙便把小說給了《北京文學》。《小說月報》轉載了《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后,引起了汪老的注意,云云。
我不知道這兩篇文章的以上說法從何而來。我以上的說法,除我當時在《北京文學》供職對情況有所了解外,還有曹乃謙發(fā)在1986年9月號《北京文學》上的《“溫家風景”初始》作為佐證,我說法中的引文便是出自這篇文章。
逝者無言。
弄清真相,對生者來說不只是一種責任,也是對逝者的一種尊重!
鑒于汪老對《北京文學》所做的重要貢獻及他眾多佳作在文壇所引起的關注,1988年9月,《北京文學》編輯部策劃了一個空前的行動――汪曾祺作品研討會。至所以說這次研討會空前,一是參加的人,不僅有吳祖緗等德高望重的學者、黃子平等評論界當紅新秀,還有美國的林培瑞、瑞典的秦碧達等國外的知名漢學家,共計20多人;二是參加者多提交有書面論文;三是這次研討會的論文以專集形式,在《北京文學》1989年第一期、臺灣《聯(lián)合文學》1989年第一期同時推出。如此規(guī)模,如此認真地研究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尚屬首次。在這個研討專集中,有汪曾祺自己寫的長文《認識到的和沒認識到的自己》。在這篇文章里,有汪老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自我定位,有對文學創(chuàng)作諸多問題的認識和主張,有自己創(chuàng)作的經驗之談,有自己創(chuàng)作思想形成的來龍去脈……我認為,這篇文章是研究汪曾祺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北京文學》在發(fā)表“汪曾祺作品研討會專集”時加的“編者按”中有這樣一段話:“從1980年震動全國文壇的《受戒》發(fā)表后,汪曾祺似乎與《北京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獲獎小說《大淖紀事》及其他許多重要作品都是陸續(xù)在本刊發(fā)表的。”
其實呢,汪曾祺與《北京文學》的不解之緣并非是從1980年發(fā)表《受戒》始,而是早得多。《北京文學》的前身是《北京文藝》,1950年創(chuàng)刊之初,汪曾祺就是編輯部的總集稿人。這總集稿人相當于后來的編輯部主任和現(xiàn)在的執(zhí)行主編吧,是主持編輯工作的實際負責人。
汪曾祺在當代中國文壇,有其獨特的重要地位。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汪曾祺一直是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之一,各家刊物都以能發(fā)表他的作品為榮。
馳騁中國文壇幾十年,若問汪老一生和哪家刊物的關系最密切,我說是《北京文學》。這樣說,可以吧?
 0
+1
0
+1